“转移前生态位”这一术语,涵盖了对未来可能转移部位的所有影响,范围从免疫调节和细胞外基质重塑,到改变血脑屏障通透性。控制转移到脑部的机制仍然不清楚。本文旨在介绍关于脑转移前生态位的最新发现,并讨论现有和新兴的进一步探索该领域的方法。
——by 周嘉炜、徐涛
转移,也称为转移性病变,是指原发肿瘤在体内通过血液循环或淋巴系统传播到其他部位,并在这些部位形成新的肿瘤。转移性病变是恶性肿瘤最常见的特征之一,尤其是脑转移瘤,这一种“毁灭性”的癌症并发症,约占所有癌症患者的20%,其缺乏有效的治疗,并且机制难以理解。倘若我们从分子基础层面入手研究,势必将找到对抗致命脑转移瘤的良策。有关“原发肿瘤如何在肿瘤细胞到达之前影响远端器官、部位”的研究已取得了重大进展,“转移前生态位”一词随之引入。虽然控制转移扩散到大脑的机制仍然难以捉摸,但是我们可通过观察转移形成中的初始步骤来逐步了解。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医院的Maximilian Geissler等人在文中介绍了脑“转移前生态位”的最新发现,并讨论了现有的和新兴的方法以进一步探索这一领域。
近年来,得益于癌前诊断和临床技术的进步,对于转移的研究,特别是脑转移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们认识到“微环境”是癌症转移发生和进展的关键因素,形成了转移生态位(MN)的概念。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发现了“转移前生态位”(PMN)——由外泌体、细胞因子、生长因子和其他信号分子的分泌共同完成。这些因素通过募集免疫细胞和基质细胞来改变靶器官细胞外基质的组成。这种“刻意”产生的微环境,为人体远处器官提供了接受循环而来的肿瘤细胞的土壤,并支持癌细胞的生存、生长和定植。下面举文中两个例子加以介绍PMN:
Kaplan等人发现,骨髓源性干细胞(BMDCs)聚集在未来发生肺转移的部位,它们上调局部纤维连接蛋白的产生过程,从而促进循环而来的肿瘤细胞的粘附。通过这种机制,原发肿瘤可以在远端产生肥沃的土壤来接受其播散的种子。自此,人们探索了许多理论上的PMN机制,以了解它们远距离修饰器官部位的能力,诸如通过上调促粘附因子改变细胞外基质以及启动早期血管生成。
内皮壁是阻断肿瘤细胞内、外渗的第一道屏障。因此,内皮在早期转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黑色素瘤和肺癌细胞对内皮细胞的重塑和细胞粘附分子的上调是通过“劫持”内皮信号传感器转录激活因子3 (STAT3)介导的。内皮细胞也可通过Notch1受体的上调而发生修饰,促进衰老和炎症,有利于转移。除此之外,在自发性小鼠乳腺癌模型中,转移前肺组织中涌入了未成熟髓样细胞,这些细胞随后通过基质金属蛋白酶9 (MMP9)重塑内皮并促进转移,这一表现可因MMP9缺失而恢复。
如前所述,原发肿瘤如何向特定器官转移以及如何形成“生态位”的机制研究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其中值得关注的是肿瘤来源的外泌体以及外泌体非编码RNA。外泌体携带具有嗜器官特征的表面蛋白,通过内皮细胞中整合素表达的变化使得一系列不同类型的癌症表现出具有器官亲和性。此外,外泌体还分别调节原发性肿瘤和转移性肿瘤的初始和后续的肿瘤微环境。外泌体非编码RNA (ncRNA)在不同肿瘤和器官中的促血管生成调节也已被充分证实,它在“转移前生态位”中起着早期效应者和调节者的作用,也正是此特点,或将为以后脑转移瘤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脑转移瘤与其他器官部位转移肿瘤本质的区别在于:肿瘤脑转移的唯一进入途径是血脑屏障(BBB),因为脑内没有可引入转移的淋巴系统。因此,想要形成“脑转移前生态位”,攻破血脑屏障防线是关键。当下研究主要聚焦的对象有三:脑内皮,旁分泌和外泌体ncRNA。它们在脑转移中的潜在作用早已被人们注意到。脑转移定植的一个早期事件是通过血小板和脑内皮细胞产生的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激活血小板,其可促进血小板聚集,并且让肿瘤细胞外溢前在血管内阻滞。此外,胶质细胞,特别是星形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是脑内皮细胞重塑的活跃介质,并被招募到未来转移的部位,它们在那里经历表型转换。
首先是脑内皮结构改变。在黑色素瘤脑转移过程中,星形胶质细胞募集涉及神经炎症和星形胶质细胞基因表达的上调,导致胶质细胞疤痕的形成和血脑屏障的破坏。Rodrigues等人证明,嗜脑乳腺癌细胞分泌含有高水平CEMIP(细胞迁移诱导和透明质酸结合蛋白)的外泌体。它增加了小胶质细胞中细胞因子的产生,具有神经炎症的作用,增加了神经血管的渗漏。该研究提到的神经炎症以及神经胶质活化一直被认为是导致肿瘤细胞根除的宿主防御反应。然而,人们逐渐认识到,转移性肿瘤细胞与血管生态位中的小胶质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小胶质细胞基因重编程和功能改变。这导致在转移定殖的各个阶段,包括血管重塑、肿瘤外渗和生长,都具有促进肿瘤的功能。同样,转移性肿瘤细胞在神经血管界面的功能选择和阻断星形胶质细胞抗癌功能的现象也有记录描述,它们的发生与肿瘤脑转移后电位增加和神经炎症反应的激发有关。
旁分泌已被发现是转移前信号的来源。例如,神经前体细胞(NPC)通过转化生长因子-β (TGF-β)家族因子BMP-2(骨形态发生蛋白)与乳腺癌细胞共培养转化为星形胶质细胞;小细胞肺癌(SCLC)分泌的胎盘生长因子(PLGF)在体外和患者样本中均被证明介导了脑内皮紧密连接结构的破坏并促进脑转移的发生,但该研究缺乏体内数据;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在体内和体外均有对血脑屏障的破坏作用;胶质母细胞瘤细胞分泌的含有VEGF-A的外泌体已被证明可以打开血脑屏障并促进血管生成,在癌症转移中也有类似的作用。
外泌体ncRNA亦被证明对未来肿瘤的转移部位有直接影响。虽然它在脑转移中的作用几乎未被探究过,但是学者们已经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在小鼠NSCLC(非小细胞肺癌)模型中,ncRNA被证明可下调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并促进肿瘤脑转移,类似地,在人类乳腺癌的体外模型中也被提出。
由于难以获得自发性中枢神经系统转移病例,因而对脑转移前组织变化的探索具有挑战性。一般来说,这需要从现有的肿瘤模型中产生嗜脑细胞系(BrM)。为了获得这些特异性细胞系,需要进行多轮肿瘤细胞接种并从阳性表达的脑中进行体内选择,使得生成的细胞系具有可靠地产生肿瘤脑转移的潜力。此外,另一个限制因素是如何在转移过程中确定合适的时间点,并使该过程尽可能接近自然生物学。由于脑转移表现的变化不像内脏转移的那么多,所以研究者们需要有检测早期脑肿瘤微转移的方法。
首先,最实际的研究策略包括肿瘤接种/注射和一定时间间隔内进行受体动物解剖,然后测量脑组织中驻留的肿瘤细胞,此策略通过薄切片组织和组织病理学分析进行,在间隔的时间点上记录组织中发现的转移细胞,确定第一次微转移发生的时间。先记录到的时间点被定义为“转移前生态位”。这种方法的好处是转移前生态位的空间重建和肿瘤外渗在组织学上的识别。但是,肿瘤生长和转移过程的生物学差异将使真正的转移前环境和明显转移灶之间的区分变困难。
其次,最近的研究表明,皮下接种表达mCherry的黑色素瘤细胞后,mCherry转录物可以在肿瘤小鼠的脑脊液中测量到,并且mCherry转录物是自发转移模型中早期微转移的准确预测因子。这种方法的明显优势是在活体动物中早期就可发现微转移,但实验可能只适用于有限的肿瘤实体,这些肿瘤实体会将细胞脱落到脑脊液中。虽然第一种方法中所介绍的“转移前生态位”的时间点可能已经过去了,但是若能在脑脊液中检测到脱落细胞,即可说明血脑屏障一定已经被破坏了。
此外,随着技术的进步,近年来“活体成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让活体多器官肿瘤细胞的可视化成为可能。新出现的转移可以被组织范围或全身的体内发光和荧光检测到;复杂的组织清晰成像法,同时结合最先进的全器官快速体积成像的显微镜,为“脑转移前生态位”早期阶段的研究另辟蹊径。
除了成像技术,单细胞测序可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强大的工具,有助于理解复杂的细胞间相互作用。它能跳脱大块组织,聚焦到单个细胞的上,为追踪观察肿瘤转移和远端器官部位的细胞组成和分子特征开辟新的视野。
“转移前生态位”的形成和其性质较为复杂。特别是在大脑环境中,研究它更需要行之有效的方法。Maximilian Geissler、Weiyi Jia等人在文章中描述了广义的肿瘤转移过程,再聚焦到肿瘤脑转移,提出“脑转移前生态位”的概念并释之形成过程,然后介绍了未来进一步对脑转移瘤研究的可用策略。鉴于没有单一的研究方法可以同时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解决“转移前生态位”的问题,跨学科研究是大势所趋,多学科间知识的碰撞擦出新的火花,这将为临床治疗提供新的方案,为患者谋福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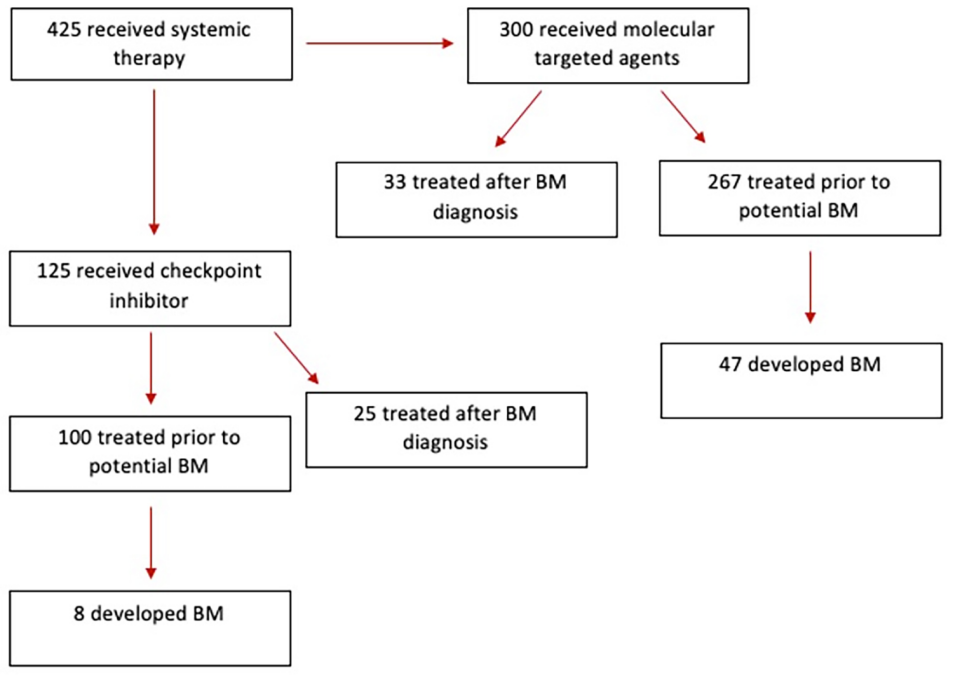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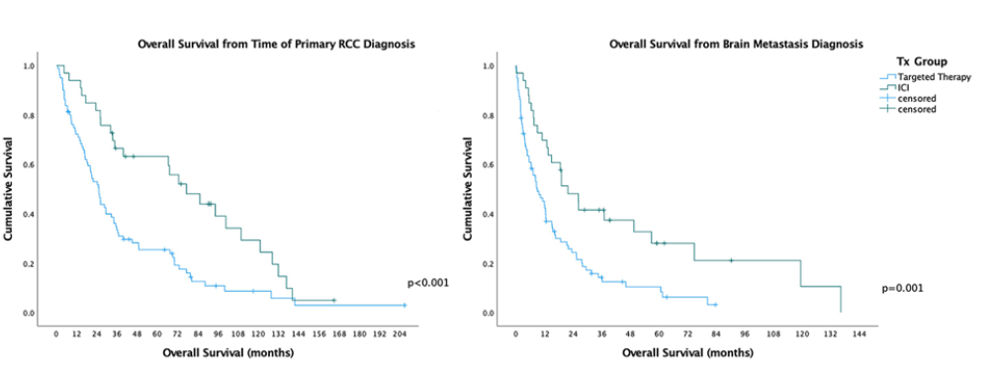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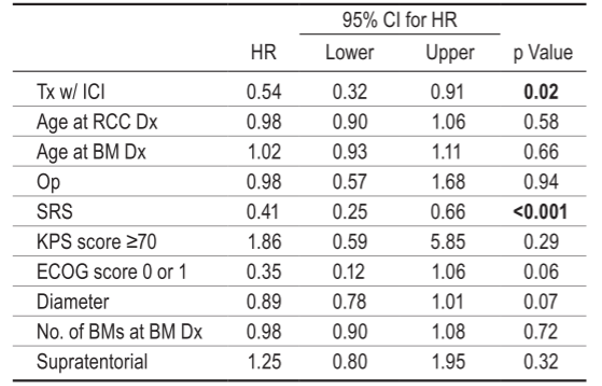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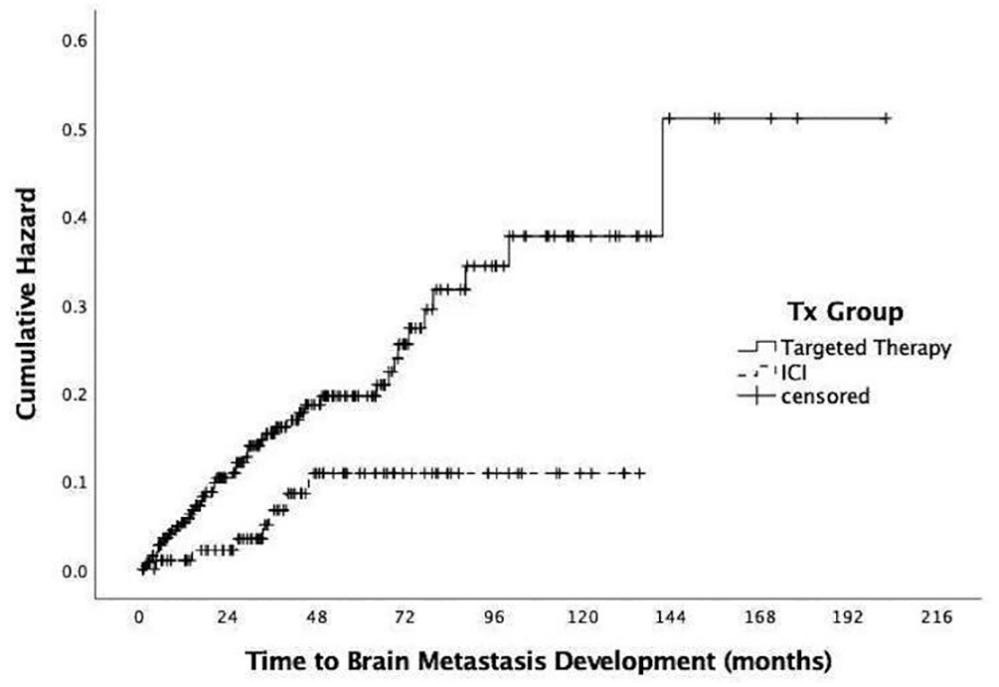
 靶点分子检测和治疗的综合建议
靶点分子检测和治疗的综合建议
近期评论